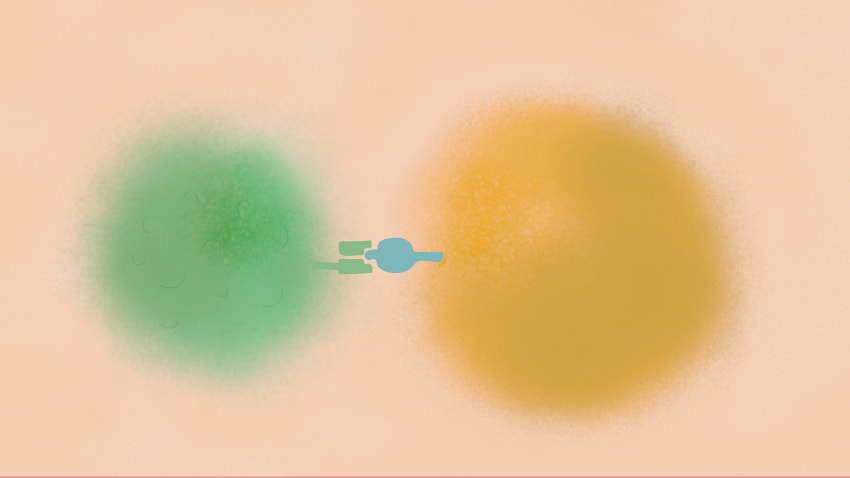对安娜堡牧师斯泰西·杜克和其他许多癌症患者来说,大流行还远未结束
杜克于2020年3月发表了个人简介,他回顾了4期癌症患者的生活,而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在关注“恢复正常”。

六月,在她50岁生日的时候,牧师。她的丈夫斯泰西·辛普森·杜克博士和他们十几岁的儿子们和其他几个亲密的家庭朋友聚在一起。
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种罕见的治疗,尽管他们都接种了COVID-19疫苗。这是因为安娜堡第一浸信会教堂的共同牧师杜克患有4期平滑肌肉瘤,这是一种在平滑肌组织中发生的罕见癌症。
更多来自密歇根州:注册我们的每周时事通讯
她说:“癌症患者,尤其是在积极治疗和免疫系统受损的情况下,感染COVID的风险更高,如果他们真的感染了COVID,那么感染COVID的可能性就更大,而且可能是致命的。”青少年也很难,他们的风险水平不一样,但他们必须像我们一样小心,特别是在第一个夏天,他们看到朋友在Instagram上社交。”
杜克今年1月庆祝了她接受4级诊断4周年,她说,过去一年半的日子充满挑战。她先来把她的经历告诉了密歇根健康博客2020年3月. 我们最近赶上了她,想了解最新情况。
杜克说:“公众有一种看法或成见,认为风险较高的人,比如癌症患者和老年人,无论如何都是一些已经脱离循环的人——而不是那些正在工作和抚养孩子的人,这当然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成见。”。
如果你在杂货店或街上遇到她,没有什么可以把杜克单独列为晚期癌症患者。她那奔放的个性、南方的风韵和学者的风趣都没有减损。
杜克说:“关于我和我的癌症,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癌症本身的症状。”问题就出在治疗上。”
对杜克来说,应对COVID的风险不仅仅是个人的,也是职业的。她和她的教会,在那里她的丈夫保罗也是共同牧师,一直在努力与何时和如何安全地返回举行当面服务。
杜克说:“我们是一个公共组织,这意味着我们不只是为内部人士服务。”我们对社区是开放的,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假设那里会有一些人的疫苗接种情况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会试图证实。所以,作为一个组织,我们的立场是,如果你在我们的大楼里,你必须戴上面具。
“我们当中最脆弱的人不得不承担风险管理的重担,这太可笑了,”她继续说癌症患者和老年人现在是小孩子了-为什么只有他们戴着口罩,因为他们不相信谁接种过疫苗?社区有责任团结起来保护我们当中最脆弱的群体。”

“可控毒性”
虽然杜克的部长级工作从面对面转向虚拟,但她也将大流行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患者宣传上,与两位医生一起工作肉瘤合作研究联盟,或SARC,以及把我算进去,同时也是肿瘤学Twitterverse的活跃代言人。
她说,在PubMed和Google将每一项新的增量研究进展带到患者家中之前,科学界似乎主要对与自己沟通感兴趣。但现在,像杜克这样的更多患者经常发现自己在努力实时跟上医学文献的步伐——新的受众致力于尽可能做出最好、最明智的决定,但有时会留下这样的感觉:他们的声音、担忧和生活经历没有在对话中得到充分反映。
像播客?添加密歇根医学新闻在iTunes或者任何你听播客的地方。
她说:“如果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是理想的,而且每个阶段的研究都是由科学家推动的,没有与病人或病人倡导者进行真正的合作,那么就少了一个真正关键的部分。”。
这一点在开发新的癌症药物时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服用药物的定性体验可能不会完全被公布的黑白数据所捕获。
杜克说:“如果你观察一种药物的毒性,客观地测量病人血红蛋白计数的下降是很容易的。”但是疲劳、疼痛、恶心和腹泻怎么办?这可能取决于患者的生活方式——对于试图抚养孩子或维持职业生涯的人来说,这是可控的吗?”
杜克希望在临床试验结果中能看到更多患者的直接反馈。
她说:“我见过的一些最好的研究甚至包括真实的病人叙述或病人引述。”而且已经有了很好的、经过验证的生活质量评估工具。”
她为那些积极尝试弥合这一鸿沟的医生们欢呼,比如医生和胰腺癌幸存者,医学博士马克·刘易斯。是Twitter上最引人注目的肿瘤学家之一,他建议其他研究人员:不要使用“可控制的毒性”一词,除非这种毒性发生在你身上时,你可以轻松地“控制”
以“保持模式”
与此同时,杜克说,她非常感谢在密歇根医学院得到的出色护理——从癌症中心迅速部署COVID预防措施,到她的肿瘤医生和护理团队在继续治疗她的疾病和探索新的治疗方案的同时给予她尽可能高的生活质量。
“我的肿瘤医生,Rashmi Chugh博士“我护理团队的其他成员都很出色,他们对我健康的关心在我和他们的每一次互动中都是显而易见的,”杜克说与4期癌症同住是一种孤独的经历,但他们对我的照顾让我知道我并不孤单。
杜克补充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他们打算帮助我尽可能长时间地活得好,他们一直在努力帮助平衡我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问题。”。“尽管如此,过去几个月还是有点像过山车。”
杜克本来计划作为患者倡导者参加今年夏天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事实上,当然——但治疗并发症让她感觉太不舒服了。
杜克现在已经参加了她的第三次临床试验,由于她的疾病罕见,很难找到。软组织肉瘤仅占所有成人癌症的1%,而且平滑肌肉瘤仅占该亚群的7-11%根据rarediseases.org。
杜克在她的第一次试验中做得非常好,其中包括化疗。从2018年到2020年,她的癌症控制了两年,但问题总是在于治疗何时停止,而不是是否停止。
她说:“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极其耐受的药物,而且副作用很小。”。
然而,化疗在2020年10月停止有效,她被转移到试验的另一部分,包括另一种药物。不幸的是,杜克经历了一种称为手足综合征的严重副作用,这种副作用使站立或移动都极为痛苦。她不会开车。
“我感觉好极了,就是走不动了,”她说。
但抛开副作用不谈,这种药最终对她不起作用。今年4月,杜克大学在圣路易斯进行了一项以放射治疗为基础的临床试验。
“我数了四次预约,”她说我有三个不同的朋友和我一起去。旅行真的很愉快,走出家门也很愉快,和朋友在一起也很愉快。”
最近,杜克参与了一项试验,该试验将一种用于治疗肉瘤的标准化疗药物与一种药物结合起来,这种药物通过靶向杜克癌症相关的有缺陷的DNA修复机制,有望帮助化疗发挥更长的作用。
但这一次,副作用更具挑战性-五种不同的主要毒性,正如医学文献所说。
她说:“我没有回到原点,但我现在正处于等待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地方。当大流行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其他人有这个优势,因为我习惯了生活在不确定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帮助我应对了这场流行病。但我也发现,无论你有多少不确定的经历,你都不会成为专家。
“也许有些人会,但我还没有达到那种开悟的程度。”
对于癌症幸存者的观点,关于癌症生活的实用建议,以及我们主要护理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注册Rogel癌症中心的Thrive通讯.